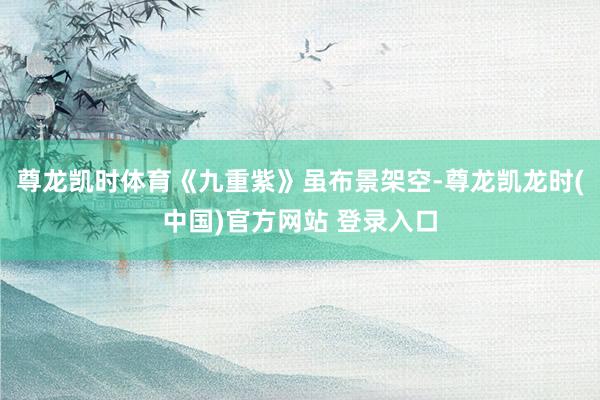
最近闲得蛋疼,扫了几眼国产古装偶像剧尊龙凯时体育,发现一个奇不雅:这年初,不结个三五回婚,都不好敬爱出来见不雅众。
远的不说,《长乐曲》开篇嫁一次,收尾又嫁一次,活像赶着完成KPI;《度华年》更狠,径直来了个“婚典三连”,不知谈的还以为是婚庆公司辅助的。

我就痛恨了,这古偶剧,如何就跟“婚典”杠上了?难谈是编剧们集体失恋,念念在剧里找安危?
这事儿,要搁曩昔,还能扯上点“东谈主生大事”、“友好邻邦”的皋比。但目下这些剧里的婚典,与其说是收复传统文化,不如说是复制粘贴的活水线产物。
大红喜服一套套地换,金碧色泽一顶顶地戴,布景音乐历久是那几首喜庆的涎水歌。就差在屏幕上打出“婚纱照相,就选××”的告白了。

你说这“替嫁乌龙”吧,历史上也不是莫得,但齐全是小概率事件。毕竟古代东谈主成婚,负责个“八字合分辨”,比目下年青东谈主看星座还认真。哪能随璷黫便就换个东谈主嫁?这要搁目下,不得被婆家告个诈骗?
还有那“接亲闯关”,更是当代婚典的入口货。古代东谈主负责含蓄内敛,哪像目下这样闹腾?真要这样搞,臆想新郎官还没进门,就被岳父大东谈主一顿板子轰出去了。

固然,我也不是完全含糊古偶剧里婚典的道理。毕竟,丽都的衣饰、笼统的场景,确乎能给不雅众带来视觉上的享受。
举例,《九重紫》虽布景架空,但其婚典场景,从金碧色泽到乌纱帽、披红,再到红帐高堂,处处可见明代婚典的影子,花轿迎亲、铜钱大雁等细节也颇具典礼感。
《柳舟记》则更侧重展现唐代婚典的丽都风仪,主角的描金织锦婚服、珍珠凤冠等细节,与《大唐开元礼》中对盛唐婚服的纪录颇为吻合。

《墨雨云间》便在唐制汉服的基础上进行纠正,新郎的乌纱帽、簪花和红色圆领袍,新娘的青色皆胸襦裙,都力争收复唐代婚典“红男绿女”的特质。
《度华年》虽是架空布景,其婚服却参考了魏晋作风,如东晋的金饰花冠、北皆的彩绘石雕等元素,展现了古代衣饰的笼统和考中婚典的持重。

这些力争收相沿代婚典的状貌,些许还能让东谈主感受到一些传统文化的魔力。但问题是,目下许多剧,只学到了外相,没学到精髓。金碧色泽是有了,但背后的文化内涵却丢得干干净净。就像一个东谈主穿了身名牌,却满口粗话,如何看都认为别扭。
更焦躁的是,目下的古偶剧,把婚典当成了激动剧情的器具。顷刻间是“先婚后爱”,顷刻间是“和亲结亲”,顷刻间又是“冲喜”。归正唯有剧情卡壳了,就安排一场婚典,准能制造点矛盾突破。

就像《长夜银河》里那场充满悬念的婚典,名义上是喜庆,实质上是为后头的逃婚情节作念铺垫。这种把婚典当“万金油”的作念法,不仅显得剧情俗套,也亏空了婚典自己所蕴含的文化价值。
说白了,目下的古偶剧,等于把“婚典”当成了一门生意。他们知谈不雅众可爱看扰乱,可爱看俊男好意思女穿华服,就拚命地往剧里塞婚典。

至于婚典背后的文化内涵,他们根底不在乎。就像那些无良商家,只念念着如何赢利,哪管你买的东西是不是假冒伪劣?
是以尊龙凯时体育,与其说古偶剧“爱重”婚典,不如说它们“爱重”婚典背后的买卖价值。红盖头一掀,全是生意。这才是古偶剧“婚典”泛滥的真相。